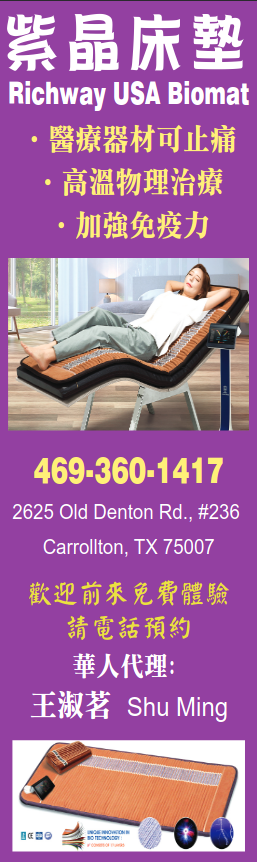【文友社】
|
中秋節,向晚時分,三個老到火候的中國人,年齡合起來是210歲,排排坐在舊金山海濱一張長椅上。端著從星巴克咖啡店買來的“拿鐵”,面對太平洋。日頭已沉沒在海平線下,霞綺顫動了最後幾下,也下班了。不識時務的霧隨即蹈波而來,覆蓋視野。
心上涌上不朽的詩句:“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落誰家?”然而,別指望看到皎洁的一輪。鋪天蓋地的是朦朧。舊金山多霧,中秋節的皎月十有七八遭它糟蹋。我們這個中國人聚居的社區,多少人的露台擺滿供果,做足功夫,線香裊進白霧,混合為一,被拜祭的月卻渺然。今晚怕又是一個主角缺失的節日,一如新娘落跑的婚禮。
不見月何妨?什麼能夠阻礙“神游”?只要一起朗誦張九齡萬古常新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只要想起故國的赤壁,那裡必高懸蘇東坡的月亮:“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万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月光光,照地堂。蝦仔你乖乖瞓落床,听朝(明天早上)阿媽要赶插秧囉,阿爺睇牛佢上山崗喔……”有人以地道粵語哼岭南童謠,渾厚的男聲。我一惊,是誰?原來是離開長椅、站在防波堤前憑欄遠望的老梁。他是當過廣播電台播音員的。就此,大洋彼岸的圓月在記憶裡冉冉上升,一起飛回遙遠的童年。禾堂或者陽台,涼席或者秋千。變聲前的嗓子,比斗歌的黃鸝還要脆亮。老余說,上四年級那陣,他剛剛削了一支彈弓。中秋節夜晚,他爬上榕樹的枝丫,對准天穹上的一輪,吼一聲“看我的!”射出一枚玻璃珠子,豪邁地對樹下仰頭的小伙伴說:“后羿射日頭,九個干掉八個。我呢,可不能把它射下來,只有一個嘛,作作樣子好了。”大家熱烈拍手。一枚艾葉做的糍糕應聲跌在地上,原來,崇拜者小丫忘記手裡拿著東西。
夜幕徐徐而下。假設老天爺突發慈悲或者管拉霧帳的大神高抬貴手,一個小時以後大霧遁跡,那麼,我們便擁有標准的晴夜。進一步,連云絮也知趣地閃避,穹窿清空,一任月輪獨自巡游在無際無涯的太平洋之上,及之下。大海溫柔以迎,波瀾緩緩卷舒,以恰到好處的節奏拍打沙灘,為我們所吟誦的古詩押“天籟”的韻。
其實,外在的風景無論怎樣,都不妨礙老興。我們要實實在在的快樂中秋,誰也阻擋不了。這就是低層次的“從心所欲,不逾矩”。該有的有了:完全由自我支配的時間,不冷的秋風,在心心相印多少年的友誼,還有,聊備一格的老年病。
這輩子,只有走到這個歲數,才做好面對大海的准備。無限,變幻,永恒,這些大得可怕的名目,都可以傲然、冷然、欣欣然解讀。不遠處的浪高起來,拍岸時聳起白發似的浪花。我高吟台灣某詩人的詩句:“沒有風,哪來的皺褶?”是啊,生途上,唯颶風、台風、龍卷風,才可能在我們的皮膚上折疊出世故、智慧和韌性。
我向著黑下去的海洋忘情一呼:“夠了!這就是我們想要的人生,這就是我們已然抵達的彼岸。”二友應和,三只手一起舉起虛擬的酒杯,以深藍如墨的天穹為背景。
生命的前一大半我們沒有大遺憾,而更加幸運的,是我們尚未完成。我站在長椅上,讓風把大衣的下擺吹成將軍的披風。我對伙伴背出歌德的《浪游者的夜歌》:
“群峰,/一片沉寂,/樹梢/微風斂跡。/林中/栖鳥緘默。”這首短章寫于1783年,是年34歲,題在伊爾美瑙的吉息爾漢山山頂別墅的牆壁上。30年後的1813年,歌德再登這座山頂,把壁上題詩的筆跡加深。又過了20年,即1831年,歌德逝世前最後一次誕辰,登山看題詩,思緒萬千,為它加上結尾:“稍待,你也安息。”
終于等來明月,人間泡在銀輝裡。我們的笑聲,與月影一起,在波浪間載浮載沉。
回上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