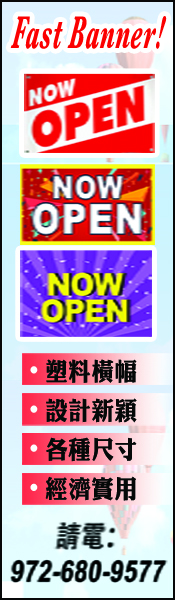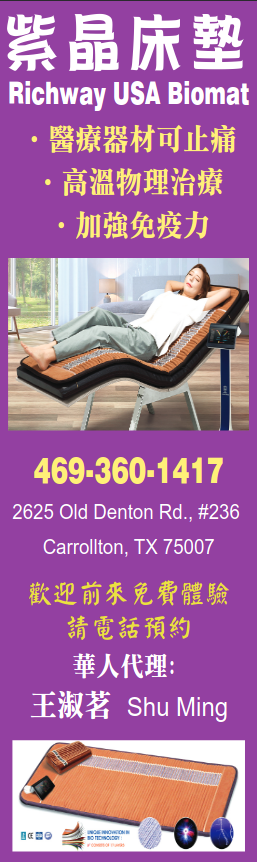【文友社】
|
“一切的虛構都消失了”
“這不是黑夜,而是光明,不是結束,而是開始,不是虛無,而是永恒。”
這是1850年秋天,偉大的法國作家巴爾紮克(Balzac)於那年8月18日去世,大作家雨果作為摯友在他的墓葬儀式上,給前來參加葬禮的成千上萬法國民眾的著名演講詞中的文采華麗而富有哲理的金句,它們表達了對這位曾經描繪了眾多文學主角的名著《人間喜劇》的作者的無限崇敬。天才作家巴爾紮克,雖然51歲就離世了,但雨果的演講,定格了這位文學巨匠藝術生命的不朽,就如他筆下葛朗臺等人物形象永遠活在全世界讀者的心中一樣。
我以幾十年前在蘭州西北師範大學閱讀法國古典文學的深刻記憶,以無比崇拜歐洲古史的心情,在維也納參加完六月底的歐華文學筆會和考遊後,便遊往了法國巴黎。第一個我急不可待參觀的是向往已久的巴黎聖母院。在此,重溫當年讀雨果《巴黎聖母院》和《悲慘世界》中的場景之地。
附近的凱旋門,它見證了當年來自法國南部地中海域科西嘉島上的拿破侖元帥的運籌帷幄,叱咤歐洲大陸,決勝千裏的風雲變幻的歷史。
輝煌的凱旋門,讓人感到拿破崙的貢獻一直在延伸至現在,予法國以恩德。已成旅遊勝地的凱旋門,給今日法國帶來巨大收入。
當然這裏還有18世紀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的雕像。霞光中閃耀著他那些哲理的詞句。
在市中心香榭麗舍大道的西段,還有盧浮宮,艾菲爾鐵塔等歷史景點。
旁邊流淌的就是那條碧綠如畫、流經巴黎市中心的塞納河。河的兩岸見證了法國的歷史,也見證了最近的一次奧運會。
從春天來臨到秋季金黃歲月的巴黎浪漫故事,河畔保留的古老式書畫品的小店,都講述著法蘭西文學藝術國度的偉大傳統——熱愛藝術,追求知識。巴爾紮克、左拉和雨果的國禮級葬禮,都在這裏隆重舉行。
法國是歐洲面積比較大的國家,包括在海外的法國領土,有60多萬平方公裏的國土。法蘭西也是一個多元包容的國度。現在巴黎的軍警中也可看到黑人、阿拉伯人和北非人,可謂是一個真正的國際大都會。
散步欣賞巴黎的大街,古老輝煌,歷史氛圍濃厚。同時法國空中巴士1971年建成,之後又造出可載500人以上的雙層空中巴士A380,這些又體現了它的高科技現代風貌。
我和太太一起遊覽盧浮宮時,還巧遇了剛一起結束維也納開會的香港作家何佳霖,也與定居巴黎的文友畫家施文英和詩人陳紅月相會,大家都喜悅不已。
在盧浮宮中心,在由美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玻璃金字塔映照下,我們一起欣賞和交流著歐洲的種種見聞軼事。
二.
我和太太拜訪了在巴黎工作生活幾十年的北京才子“四陳之一”的陳超英先生,他目前正在撰寫全十卷《法蘭西史》。我閱讀過他已經出版的前三卷。
陳超英的曾祖父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的“二陳”之一的陳垣,曾擔任過北京師範大學校長,擔任過46年之久的大學校長,從事文化工作70年,也擔任過北京圖書館長、故宮圖書館館長。陳垣還是大書法家啟功的老師,啟功在世時一直感念陳校長的伯樂知遇之恩。
而陳超英的祖父陳樂素是日本史研究專家,其父親陳智超是宋史學家。
陳超英則是第四代,他有先輩的血緣繼承與文脈傳承,他的鴻篇巨制《法蘭西史》,將續寫陳家事業的新篇章!
陳超英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來歐洲生活,在巴黎白手起家,有著非常豐富的生活經歷。但為了撰寫《法蘭西史》,他只好離開了自己經營的生意,專心致誌於著書立說,其人格的超越和境界的升華,令人非常佩服。
在澳洲我們一起參加過世界華人筆會,會下一起喝茶談笑,那時我就感到他為人的真誠與坦率。
他著作的作者介紹部分,顯示他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包括看門人、司機、一般勞工到後來自己開旅行社等等。這次,他聽到我與內人要來巴黎,提前就安排晚宴一聚。後來,聽說我是回民,只吃清真,為此專門預訂巴黎著名的黎巴嫩餐廳。這體現了他對我們的傳統習俗的尊重,為此我確實很感動。
在黎巴嫩餐廳與他的女朋友一起,我們大家都非常高興,非常開心。畢竟我們有過共同的經歷,那就是我們都是八十年代出來海外的,有相同的背景,有許多相同的拼搏經歷,都是白手起家,經商後又繼續做文化研究、回歸學術與寫作。
三.
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四陳”指的是他們四代人,即第一代曾祖父陳垣,也稱呼為新會(廣東的)陳垣;第二代祖父日本史專家陳樂素;第三代父親宋史學家陳智超;第四代他本人陳超英,正撰法國全史。古今中外這樣的四代名人還是比較少見的。
我說巴黎早期有著名的“三仲馬”,即老仲馬(1786-1806),拿破侖時期的將軍;大仲馬(1802-1870),《基督山伯爵》和《三個火槍手》的作者;小仲馬(1824-1895),因寫《茶花女》而聞名。《茶花女》早在1899年由福建人林紓翻譯到中國,影響深遠,連當時的改革派嚴復說:“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對於“仲馬”的翻譯,是按照閩南語翻譯的。仲馬即大仲馬的母親名字,是其父老仲馬在海地娶的黑奴女子。而小仲馬則是大仲馬與工作坊認識的女裁縫所生的。
中國古代最有名的一家出仨名人的,如漢代“三曹”(155-232期間的曹操,曹丕,曹植),宋代的“三蘇”(即蘇詢,蘇軾和蘇轍)。三仲馬為三代人,而“三曹”和“三蘇”則是倆代人。
那麽現代以來出現“四陳”,即陳垣,陳樂素,陳智超和陳超英屬於四代文化精英。同時,陳家也有倆巾幗,超英的祖母洪美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坐飛機的女性,1915年6月,其祖母在香港坐上雙翼飛機,為當時廣東水災義飛。而其母親曾慶瑛,彜族,也是人民大學教授和作家。
應該說,這一家四代包括巾幗英雄在內的海內外的文化精英家庭,也算是罕見的文化家族。
讓我感動的是超英兄,是從巴黎60多公裏郊外的家,坐地鐵來市中心招待我們的。
巴黎的地鐵交通與日本一樣,四通八達,車票有一次性的,也有全天的,即一天無數次使用票,非常方便。
然而,巴黎,包括歐洲,讓華人朋友特別是導遊類職業的人,感到特別頭痛的事,就是總需不斷重復提醒防盜防搶的警告,需防護照、銀行卡和現金被盜。旅遊本來是一個愉快輕松自在的事,然而現在去歐洲卻是要一路防備著。
1799年,有法國大革命。我認為歐洲現在應該有一次“除盜除搶的大革命”。
在美麗的巴黎夕陽余暉中,我們離開了這個難忘的歷史名城。那些記憶猶新的歷史光輝,如巴黎西邊夏日的金黃色餘輝,銘刻在我們的心裏。
路上我一直重溫著陳君書封底上的一句名言,它正刻在巴黎人類博物館的牆壁上:
我們是誰?(Qui Sommes -Nous?)
我們從哪裏來?(D\'ou Venons- Nous?)
我們要到哪裏去?(Ou Allons -Nous ?)
這是我們現代人的終極困惑!
作者簡介
劉寶軍,馬來西亞華人作家,早期畢業於中國西北師範大學中文系,後分別獲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社會學雙學士及教育學碩士學位。出版40部作品(包括華文,英語和馬來文),五次獲得馬來西亞寫作優秀獎。
回上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