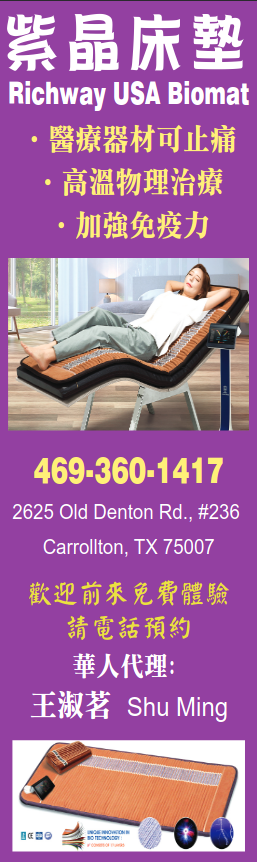【文友社】
|
新中國的第一代人幾乎都讀過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書中主人公保爾·柯察金的一段話深深影響了那一代人: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屬於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迴首往事時,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終時,他能夠說: ‘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
這段話道出了一種嶄新的人生觀,激勵著新中國第一代人追求有意義的人生。沒有人願意虛度光陰或碌碌無為,人們都渴望為崇高的事業而奮鬥。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到來打亂了一切。曾經的理想被批判為修正主義,人們陷入迷茫,無所適從。
隨著運動浪潮的激盪, “上山下鄉”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1700萬年輕人因學校停課而奔赴農村和邊疆。這裡,我想分享一首詩——郭路生的《相信未來》。這首詩寫於1968年,那年年底,我前往山西雁北農村插隊。1966年文革開始後的兩年,社會動盪,學校關閉,圖書館封門, “文化”的大門也隨之關閉。唯一敞開的是通往農村的路。那時,我們這一代人都在討論“去哪兒?” ——有人去了東北,有人去了內蒙,有人去了雲南。不論身在何處,《相信未來》這首詩幾乎是每個知青心中的共鳴。
離開北京時,火車站鑼鼓喧天,陽光燦爛,但我的內心卻陰雲密佈。天蒼蒼,夜茫茫,人生的意義何在?未來的路通向何方?正是這首詩,如同暗夜中的一盞明燈,照亮了我迷茫的心靈。其實,我是在農村插隊後才讀到這首詩的。它的意境瞬間觸動了我的心弦。那一刻的感受,彷彿凡爾納小說《格蘭特船長的兒女》中的艾爾頓,被遺棄在太平洋荒涼的塔博爾島上,日日眺望遠方的船隻,期盼被帶離孤島。精神的力量在那個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顯得尤為強大。
《相信未來》的作者郭路生與我們年齡相仿,寫這首詩時年僅20歲。他曾說: “文革前我就已歷經磨難,我看到了這一代人的命運。魚兒躍出水面,落在冰塊上,它的前途是死亡,與冰塊一同消亡,卻看不到冰塊的消亡。後來我寫下《相信未來》,相信我們能戰勝死亡,這是一種進步。我年輕,我能看到冰塊消亡的那一天。”
我將《相信未來》抄寫在一個“時代”筆記本上,那本筆記本裡還記錄了無數豪言壯語——從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人生感言,到齊奧爾科夫斯基的仰望星空,從毛澤東的“風流人物看今朝”,到俾斯麥的“不忘東方”。許多人都有這樣的筆記本,從插隊到上大學,從青春年少到出國前夕。可惜,我的筆記本後來丟失了,但那些記憶卻永不磨滅。那段歲月,刻骨銘心。
《相信未來》——郭路生
當蜘蛛網無情地封鎖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余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當我的紫葡萄化為深秋的露水,
當我的鮮花依偎在別人的情懷,
我依然固執的凝霜枯藤,
淒涼的大地上寫下:相信未來。
我要用手指那湧向天邊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陽的大海,
搖曳著曙光那枝溫暖漂亮的筆桿,
用孩子的筆體寫下:相信未來。
我之所以堅定地相信未來,
是因為我相信未來人們的眼睛,
她有撥開歷史風塵的睫毛,
她有看透歲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們對於我們腐爛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悵、失敗的苦痛,
是寄予感動的熱淚、深切的同情,
還是給予輕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諷,
我堅信人們對於我們的脊骨,
那無數次的探索、迷途、失敗和成功,
一定會給予熱情、客觀、公正的評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著他們的評定。
朋友,堅定地相信未來吧,
相信不屈不撓的努力,
相信戰勝死亡的青春,
相信未來,熱愛生命。
這首詩是我在知青歲月裡的精神支柱。它讓我相信明天會更好,這種對未來的期盼賦予了我無窮的力量,支撐我走過人生的低谷。回想那段上山下鄉的日子,思考人生的意義,至今仍令人回味無窮。
多年後,我讀到了維克托·弗蘭克爾的《活出生命的意義》。作者是一位二戰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他提出了一種全新的觀點:支撐人類在極端苦難中活下去的是對生命意義的體認。這讓我耳目一新,同時也讓我意識到,這不正是保爾·柯察金精神的延續嗎?
1942年,33歲的弗蘭克爾新婚不久,卻被納粹士兵強行帶走,關進奧斯維辛集中營。從受人尊敬的醫生淪為編號119104的囚犯,他面對毒打、饑餓和死亡的威脅,親人相繼喪生,自己也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在極端環境中,弗蘭克爾發現,支撐他活下去的不是對未來的幻想,而是對生命意義的感悟——對家人的愛和一定要活下去將經歷訴諸世界的使命感。獲得解放後,他將這些感悟發展為“意義療法”,提出人類最根本的驅動力不是享樂或權力,而是追求意義。這本書因此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之一。
讀《活出生命的意義》時,我不禁聯想到郭路生的《相信未來》。這兩部作品雖源於截然不同的歷史背景,卻都深刻揭示了人類在逆境中尋找活下去的理由。弗蘭克爾強調體認生命意義是承受苦難的關鍵,郭路生的《相信未來》則如一盞希望之燈,激勵知青一代在迷茫與困苦中前行。
《相信未來》創作於文革期間,那是一個社會動盪、思想混亂的時代。1700萬城市青年下鄉接受“再教育”,遠離城市,未來充滿不確定性。郭路生在詩中表達了對未來的堅定信仰,成為一代人的精神支柱。詩中寫道: “當蜘蛛網無情地封鎖了我的爐台……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這種對未來的期盼為知青們注入了力量,讓他們在物質匱乏和精神壓抑中找到希望。
儘管弗蘭克爾的集中營經歷與知青的下鄉歲月不可同日而語,但兩者都代表了人類在極端環境中的掙扎。弗蘭克爾面對的是生死考驗,而知青們面對的是青春的迷失和未來的未知。無論是對意義的體驗還是希望,這兩種精神力量都在幫助人們超越苦難,找到生存的理由。
讀《活出生命的意義》時,我的知青歲月已成為過去,人生經歷更加豐富,認知能力也遠超插隊之初。因此,我能更深刻地感受到,這本書比《相信未來》更具哲學深度。弗蘭克爾提出,生命的意義不在於懊悔過去或幻想未來,而是在於在當下苦難中找到奮鬥的目標。他發現,集中營中存活下來的人往往不是身體最強壯的,而是那些找到意義的人。例如,他通過思念家人和未來的使命感,賦予了自己忍受痛苦的理由。他還講述了一位失去妻子的老人,沉浸在悲痛中無法自拔。弗蘭克爾引導他認識到,生存的意義在於代妻子替她承受痛苦,讓她免受悲傷。這種意義感讓老人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
意義療法強調“活在當下”,鼓勵人們接受苦難的現實,並在其中尋找意義。弗蘭克爾認為,苦難並非毫無意義,而是通向成長的必經之路。他寫道:“唯有意義才能指引人們走出困境。”這種理念與單純的“希望”形成鮮明對比。他提到一位號長因夢到聖誕節獲釋而燃起希望,卻在聖誕節未獲解放後精神崩潰,迅速去世。單純的希望可能帶來不切實際的幻想,一旦幻想破滅,精神支柱也會崩塌。
郭路生的《相信未來》傳遞了一種對未來的樂觀信念,充滿了對苦難的直面和對未來的憧憬:“我堅信人們對於我們的脊骨,那無數次的探索的、迷途、失敗和成功,必定會給予熱情、客觀、公正的評定。”這種信念為知青們提供了精神寄託,讓我在迷茫中找到方向。然而,希望的力量並非萬能。單純的希望可能導致失望,甚至絶望。郭路生在也坦言: “魚兒躍出水面,落在冰塊上,它的前途是死亡,與冰塊一同消亡,卻看不到冰塊的消亡。”這表明希望雖能激勵人前行,也可能讓人忽視當下的現實。
儘管意義與希望有所不同,它們在實踐中的作用卻常常交織。弗蘭克爾的意義療法並非否定希望,而是強調希望必須建立在意義之上。他在集中營中的堅持,源於對家人的愛和未來的使命感,這本質上是有目標的希望,而非空洞的幻想。同樣,郭路生的《相信未來》以希望為核心,但也流露出對當下奮鬥的肯定:“相信不屈不撓的努力,相信戰勝死亡的年輕。”這種努力正是意義療法倡導的在當下尋找目標的表現。
兩者都體現了珍惜當下、奮鬥不息的精神,在苦難中尋找超越自我的目標,既是對未來的期盼,也是對當下的堅守。弗蘭克爾說:“找到生命的意義,不懊悔過去,不覬覦將來,帶著這份意義感做好當下的每一件事。”這種理念不僅幫助他存活下來,還將戰後經歷轉化為幫助他人的力量。
總之,苦難並非毫無價值。它不僅是身體的考驗,更是心靈成長的契機。正如詩人顧城所言:“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要用它尋找光明。”知青年代的苦難經歷,宛如挖掘金礦時遇到的一堆堅石瓦礫,唯有堅持挖掘,才能發現生命的寶藏。
回上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