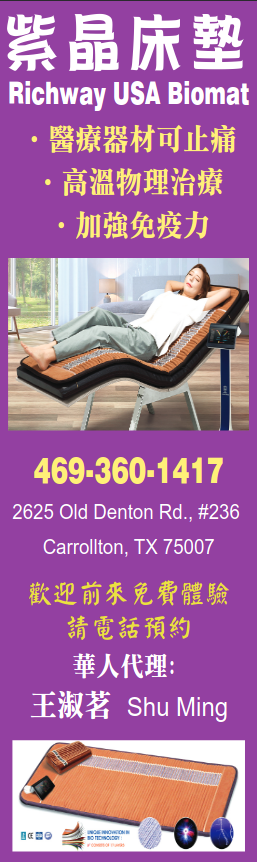【文友社】
|
天明,樊天明,我兩歲就認得他了。
那時,我無聊時,就去街頭右手邊的拐角,那裡是一家鐵匠鋪。
我喜歡看爐門打開時,轟轟響的金黃火焰,竄騰跳躍;喜歡看鐵匠從火焰裡夾出一塊燒得通紅的鐵,放在鐵砧上捶打。左手的鉗子夾住鐵塊,右手的鎚子不斷舉起砸下,每捶打一下,左手的鉗子就翻滾一下。火紅的鐵塊,在猛力捶打下,會濺起火星,有的火星會飛出老遠,我的手臂就被火星針刺般燙過幾次,但我還是喜歡看。
這時候,鐵匠裡有個溫和的聲音說:“小朋友,跑遠點,當心燙著你。”
也有鐵匠惡狠狠地說:“這是啥人家小孩,怎麼沒人管?”或者一聲吆喝:“小赤佬,跑遠點。”
那個說話溫和的告訴說話凶的:“他是吳貴富的兒子。”
說話溫和的叫天明,樊天明。
有一次看見我來了,他從背帶式的工裝褲袋裏摸出一塊奶油糖給我。
我從小就能根據大人對小孩的態度,準確判斷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天明,樊天明是好人。
不久,鐵匠鋪消失了。
那年頭,小街上的店舖,一間接著一間的消失。
鐵匠鋪對面的大餅油條店消失了。
隔壁的煤球店消失了。
我家弄堂口隔壁的麵店消失了。
我本來每天出弄堂口,就看見麵店外婆搖著切面機搖出切面。維玲姐在自家窗口賣竹匾裡的面。
搖面機搬走了。
從大人口中得知,公私合營了。那些消失的店舖,都公私合營了。
外婆已經不能在自己家裡搖面,她每天天不亮就起來,邁著行走緩慢的小腳,走個把小時,去小南門麵店上班。冬天裡滿手凍瘡,手指節、手背,又紅又腫,腫得開裂流血。
隨著鐵匠鋪一起消失的天明,又在小街出現了。並且成了我家鄰居。
他和維玲結婚了。
他們結婚那天,我沒參加婚禮,也得到了一袋喜糖。
那年我五歲。樊天明二十二歲。
天明成為我家鄰居後,我才看到他不穿背帶工裝褲的樣子。
他在一家醫療器械廠上班。他的休息日不是禮拜天,是禮拜二。
每到休息日,早飯後,他去浴室泡澡,然後去理髮店理髮吹風。吹成一個包頭,還打了髮蠟。
穿著筆挺的嗶嘰中山裝,冬天會在外面套一件呢大衣。襯衫領口永遠是雪白的。
天明很孩子氣。他為自己的風度翩翩得意。當著維玲的面,告訴我們,女人們怎麼回頭看他。維玲就笑,罵他十三點。維玲很為自己的老公得意。
天明長得確實英俊,尤其是鼻梁,那麼挺。中國人裡面很少見。
最體現天明孩子氣的,是他每年夏秋之交,喜歡養蟋蟀、鬥蟋蟀。他喜歡了一輩子。
我就是受他影響,也喜歡養蟋蟀鬥蟋蟀。
天明把如何判斷蟋蟀好壞,如何養蟋蟀的招數傳給我。
他鬥蟋蟀,不分大人小孩。外婆看到他埋頭在小孩堆裡就生氣,講他沒大沒小,不知分寸。
天明孩子氣,還表現在他有時喜歡炫技。
有年夏天,他兩手捧著西瓜,不扶把手,騎著腳踏車回家。雙脫手騎腳踏車,我後來也學會了。但是,天明居然還能捧著西瓜,從馬路上拐彎進入小街,在自己家門口穩穩停下,引得在街上乘涼的一片驚奇。
這本事,我後來努力了很多次也沒學會。
文革期間,學校停課,工廠停工。閒著沒事幹,颳起一股養熱帶魚的風氣。
天明做的養魚缸,連十六鋪的人都跑來參觀。
魚缸裡各種名貴熱帶魚和綵燈不說,養熱帶魚需要恆溫,他的魚缸下面是兩個鐵皮做的小抽屜,拉開抽屜,裡面燃著木屑。
後來又颳起自製煤油爐的風氣。天明做的煤油爐,是不銹鋼打造的宮燈形狀。底座倒油口,他可不像別人那樣只是一個簡單的木塞子,而是用不銹鋼做成漂亮的蓋子,蓋子上是鉸鏈狀不銹鋼鏈條,與煤油爐合成一體。
打鐵屬於粗活,天明的手怎麼這麼巧呢?
天明是常熟人。12歲就離家出來學徒。他沒有讀過書,不識字,但是他能看懂複雜的工藝圖,並且完美的加工製造出來。
文革前他就是七級模具工,工資八十六。那年頭,工人階級工資大多只有五六十。
天明不僅能看懂工藝圖紙,他還能自己畫圖紙。他畫的方法很特別,用粉筆在草紙上畫。然後他就能根據自己畫的這種另類工藝圖,開出模具來。
有一次,他拿著一本名叫技術革新的雜誌給我看,上面刊登著他發明的磨刀棒。醫用手術刀,只要在磨刀棒上刮幾下就鋒利了。
還有一次,他從瀋陽出差回來。講了他去瀋陽的故事給我聽。
上海衛生局從英國進口了一台細胞切片機。因國家外匯緊張,無法多買,就把這台機器交給他仿製,天明不僅仿製成功,還比進口的體積縮小了百分之二十。
瀋陽醫療器械廠按照他的工藝流程仿製,結果失敗。就通過單位把他請去指導。他去了之後,從一塊不銹鋼開始,從頭做到尾,做成了細胞切片機。
瀋陽醫療器械廠廠長觀看了整個過程之後,明白了複製失敗的原因。他們是把整個工藝分別給不同人做,由於機床達不到零部件所要求的那種精密度。最後組裝的時候,就無法合成。而天明是從頭到尾一人獨自完成,哪個零部件有偏差,他就在其它方面彌補一點。這樣最後還是能組裝起來。
大饑荒年代,天明利用晚上或者休息日,在地下作坊,做爆米花機賺外快。
1965年當局搞四清運動,查獲了地下作坊,天明因此不僅在單位被批鬥,還被罰了款。
改革開放後,天明好日子來了。民營企業最缺的就是高級模具工。他到處被人請去好吃好喝招待,還拿高工資。一直幹到七十多歲,才徹底退休。江浙一帶的鄉鎮企業,都稱他為上海師傅。天明晚年為上海爭了光。
2021年夏天,想起多年不見的天明和他的兒女,我請妹妹洪英出面邀請他們全家,還有另外兩家老鄰居,一起到天明居住的浦東塘橋附近的飯店,大家聚聚。
天明和維玲以及外婆都好客。每年春節必舉辦家宴,宴請天明的同事朋友。他們三人,從春節前就開始為家宴忙。
天明每年這個時候會親自下廚。天明在燒菜方面也是一把好手。
有一次他一面做白斬鷄,一面向在旁觀看的我,傳授把白斬鷄做得鮮嫩的訣竅。還特別交代,上桌前一定要放上香菜,顏色搭配才好看。再說,香菜本來也好吃。
那個年頭,什麼都要憑票。香菜也只有過年才有得賣。而且要五角一兩。五角可以買十斤青菜了。
我成人後喜歡下廚做菜,和天明的影響分不開。
天明家每年春節必舉辦家宴。每年家宴必邀請我。我十五歲起就代表父母,成為天明家宴的座上賓。
年年如此,除非過年沒回來。
天明的家宴,不僅讓我享受到豐富的美食,還使得我早早懂得了宴席禮儀。
楊渡街1995年動遷後,老鄰居四散各處。
我家和天明家雖然一直保持聯繫,但是見面一年比一年少。
維玲和外婆已經不在人世了。老天明現在怎樣了?
我1970年去江西插隊落戶後,回來探親,發現我小弟一輩,把天明改為老天明,和我們直呼天明的叫法不同了。
那天飯局,因天氣炎熱。天明吃得很少,不過相談甚歡。
席間說起當年一段往事:我大弟放學回家的擺渡輪上,遭受一個小流氓欺負,氣得飯也吃不下。我就拉上他,衝到小流氓家,把他狠揍一頓。小流氓的姐姐就叫喚來一大群小流氓追打我們。我和大弟分頭逃跑。他逃到附近大伯家,我往自己家逃。快到自己家弄堂口,被成群小流氓追上了。幸虧這天是天明休息日。他趕緊衝過來,伸開兩臂一攔,把我擋在他身後。他打鐵出身的雙臂十分有力,一攔再加一推,小流氓頓時跌倒了四五個。小流氓遇到武藝高強的人,頓時老實了,乖乖撤退。
聚會時我對老天明說,那天要不是你出面,我可能被打殘了。
其實,天明對我的恩情何止這一件!
作者簡介:吳洪森,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知名政論家。
回上一頁